【名人故事】宏观经济先知——扬·哈齐乌斯
2006年盛夏的华尔街,阳光透过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,洒在一片狂欢的金融市场上。当时美国房价已连续10年上涨,次级房贷规模突破1.3万亿美元,投行们忙着将MBS(抵押贷款支持证券)包装成“低风险高收益”产品,对冲基金经理们在酒会上吹嘘“房价永远不会跌”。就在这样的狂热中,高盛一位名叫扬·哈齐乌斯的经济学家,却在8月发布了一份震惊业界的报告——《美国住房市场:拐点已至,风险将蔓延至金融体系》。

报告里,哈齐乌斯用一组冰冷的数据打破了泡沫:2006年二季度,美国次级房贷违约率已从1年前的5.8%飙升至8.9%,而发放的次级贷中,“零首付、无收入证明”的“忍者贷”(NINJALoan)占比达42%;更关键的是,他通过自己构建的“家庭债务可持续模型”测算,若房价下跌10%,将有120万户家庭因资不抵债断供,进而引发MBS资产贬值,冲击整个金融体系。

这份报告在当时遭到了几乎所有人的质疑。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公开反驳:“哈齐乌斯的模型太悲观,美国经济韧性足以支撑房价平稳增长。”甚至高盛内部的交易部门也抱怨:“这份报告让我们的MBS销售业绩下滑了20%。”面对争议,哈齐乌斯没有退缩,他在后续的月度报告中持续更新数据——2006年12月,他将房价下跌预警上调至20%,并明确指出“投行的高杠杆会让风险放大10倍”。

18个月后,预言成真。2008年3月,贝尔斯登因持有大量有毒MBS倒闭;9月,雷曼兄弟破产,次贷危机全面爆发。此时华尔街才回头翻看哈齐乌斯2006年的报告,发现他精准预判了危机的传导路径——从房贷违约到资产贬值,再到金融机构流动性枯竭。这份“逆声预警”不仅让高盛提前调整了资产配置,减少了近50亿美元的损失,更让扬·哈齐乌斯这个名字,从此与“宏观经济先知”画上了等号。
这场预警并非偶然,而是哈齐乌斯三十余年宏观经济研究的必然结果。从德国小镇的经济学学生,到美联储的分析师,再到执掌高盛全球经济研究部门,他的人生轨迹,始终围绕着“用数据穿透市场迷雾,用理性对抗情绪狂热”的核心逻辑。

1967年,扬·哈齐乌斯出生于德国科隆一个普通家庭。少年时的他就展现出对数字的敏感,高中时期数学与物理成绩始终稳居年级前列。1986年,他考入德国波恩大学,主修经济学与统计学——这所诞生过6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学府,以“严谨的数据分析”和“实证研究传统”闻名,正是在这里,哈齐乌斯奠定了“不唯理论、只唯数据”的学术底色。

大学期间,他的毕业论文聚焦“德国战后通胀与失业率的关系”,通过梳理1950-1988年的月度经济数据,提出“通胀率超过5%时,失业率每下降1%,将导致后续通胀加速上升”的观点,这一结论后来被德国央行纳入货币政策参考框架。导师评价他:“哈齐乌斯总能从看似杂乱的数据中找到隐藏的逻辑,他不相信‘完美理论’,只相信‘数据验证’。”
1990年,哈齐乌斯获得硕士学位后,远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,师从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劳伦斯・萨默斯(后来的美国财长)。萨默斯的“宏观经济平衡理论”深刻影响了他——即宏观经济的稳定,依赖于就业、通胀、贸易收支三大指标的平衡,任何一个指标的严重偏离,都会引发系统性调整。这段求学经历,让哈齐乌斯从“数据分析师”向“宏观洞察者”转变。

1994年,27岁的哈齐乌斯博士毕业,加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(美联储),担任经济研究部分析师。在美联储的三年里,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分析全美各州的就业数据、通胀指标、企业投资情况,为美联储利率决策提供数据支撑。这段经历让他深刻理解了“宏观政策如何影响资产价格”:
1996年,美国科技股开始出现泡沫迹象,哈齐乌斯通过分析“企业盈利增速与股价涨幅的偏离度”,发现当时纳斯达克指数的涨幅是企业盈利增速的5倍,远超历史均值。他在内部报告中建议“警惕资产泡沫风险”,虽然当时美联储并未立刻加息,但这段经历让他意识到:“市场情绪往往会偏离经济基本面,而宏观分析师的职责,就是指出这种偏离。”

在美联储的工作,还让哈齐乌斯学会了“从政策细节中预判趋势”。比如他通过跟踪美联储的“贴现窗口贷款规模”,提前察觉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美国金融机构的冲击——当时美国银行向美联储的贴现窗口贷款量突然增加30%,说明银行间流动性开始紧张,这一信号后来被证明是美国经济受亚洲危机影响的早期预警。
1997年,哈齐乌斯离开美联储,加入高盛,担任欧洲经济研究主管。当时欧洲正处于欧元诞生前夕,市场对欧元的汇率走势、欧元区经济协同性充满疑问。哈齐乌斯带领团队构建了“欧元区经济协同模型”,通过分析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等国的通胀差异、财政赤字、贸易往来数据,预判“欧元初期将面临贬值压力,但长期会因区域贸易整合而走强”——这一判断与后来欧元的走势完全吻合(1999年欧元兑美元从1.18跌至0.82,2002年后逐步回升至1.60)。

2002年,哈齐乌斯调任高盛美国首席经济学家,开始聚焦美国房地产市场与信贷风险。他发现一个被市场忽视的细节:2003年后,美国次级房贷的审批标准持续放宽,2004年“零首付”房贷占比仅15%,2005年飙升至30%,2006年一季度更是达到42%;同时,房贷利率从固定利率转向浮动利率的比例,从2003年的20%增至2006年的65%。
“这是典型的‘风险累积’信号。”哈齐乌斯在2005年的内部会议上提醒,“浮动利率意味着,一旦美联储加息,购房者的月供将大幅增加;而零首付意味着,购房者没有任何‘安全垫’,房价稍有下跌就会资不抵债。”2006年,当美联储将基准利率从1%上调至5.25%时,哈齐乌斯立刻意识到“违约潮即将来临”,于是便有了那份震惊华尔街的次贷预警报告。

2008年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,哈齐乌斯并未停留在“验证预判”的成就感中,而是迅速转向“危机应对与经济复苏路径”的研究。他在2009年发布的《美国经济复苏蓝图》中,预判“美国经济将进入‘缓慢复苏’,失业率会维持高位(8%以上)至少3年,美联储将维持低利率至2014年”——这一判断后来被事实验证,美国失业率直到2012年才降至8%以下,美联储也确实在2015年才首次加息。

2010年,当市场还在关注美国经济复苏时,哈齐乌斯又将目光转向欧洲,发布《欧债危机:从希腊蔓延至欧元区核心国家的风险》。他通过分析希腊、西班牙、意大利的政府债务与GDP比率、财政赤字率,指出“希腊债务违约只是开始,西班牙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将引发更大危机”。2012年,西班牙银行业危机爆发,验证了他的预判,高盛也因此提前调整了欧洲资产配置,避免了近30亿美元损失。

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初期,市场陷入恐慌,有人预测“美国经济将陷入大萧条级别的衰退”。哈齐乌斯却通过分析“疫情防控措施对经济的冲击半径”“财政与货币刺激力度”,发布报告《疫情下的经济:V型复苏可期》,预判“只要政策支持到位,经济将在疫情缓解后快速反弹”。2021年,美国GDP同比增长5.7%,创下1984年以来最高增速,再次印证了他的判断。

如今,扬·哈齐乌斯已担任高盛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兼全球投资研究主管,他带领的团队连续12年被《机构投资者》杂志评为“全球最佳宏观经济研究团队”,他本人也成为各国央行、主权基金、大型机构投资者的“宏观经济顾问”。

扬·哈齐乌斯在2022年的高盛全球投资峰会上曾说:“投资的本质不是预测短期价格波动,而是理解宏观经济变量如何驱动资产的长期价值——通胀、利率、就业、政策,这些才是决定资产价格的‘底层代码’,而非市场情绪或短期热点。”这句话既是他三十余年宏观研究的核心总结。

扬·哈齐乌斯的故事,从来不是“预测大师”的传奇,而是“数据驱动、理性分析”的宏观研究典范。他教会我们:宏观经济不是抽象的理论,而是能直接指导投资的“底层代码”;而贵金属也不是单纯的“避险工具”或“投机品种”,而是宏观变量(利率、通胀、政策、产业)共同作用的“价值载体”。
对贵金属投资者而言,哈齐乌斯的启示在于:
1.放弃“短期猜涨跌”的执念,像他一样,花时间研究“通胀数据、央行政策、工业需求”这些宏观与产业变量——这些才是决定贵金属长期价值的关键;
2.建立“风险预警机制”,像他提前预警次贷危机那样,当贵金属价格偏离宏观基本面(如黄金在实际利率上升时仍暴涨),要警惕风险;
3.拒绝“情绪化跟风”,像他在华尔街泡沫中坚守数据理性那样,不被“黄金永远涨”“白银将翻倍”的传言迷惑,用数据验证每一个投资决策。

扬·哈齐乌斯曾说:“宏观经济的魅力,在于它能让你看清市场的本质,而非被表象迷惑。”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贵金属投资——当你能像哈齐乌斯一样,从宏观数据中找到贵金属的“价值锚点”,就能在波动的市场中保持清醒,实现长期稳健的投资回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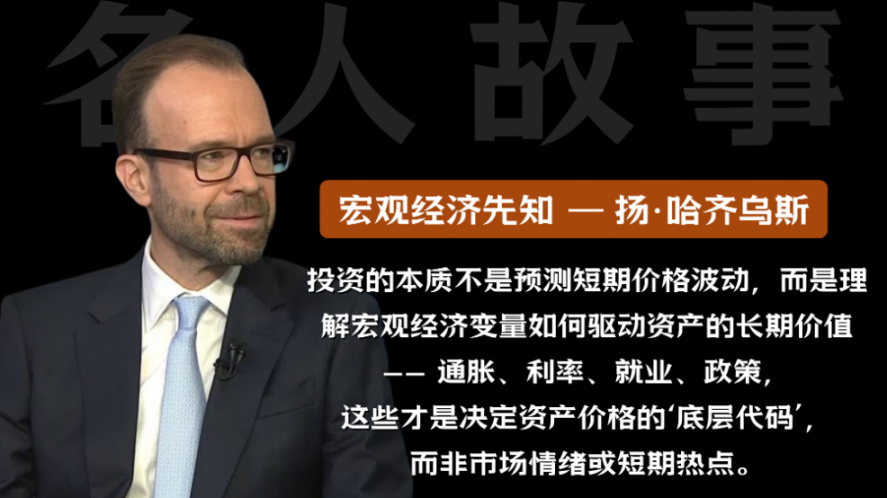
别打CALL,打赏
• 遵守当地法律、法规,尊重网上道德,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法律责任。
• 此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并不构成投资建议,投资有风险,入市需谨慎。
• 请勿留下任何个人联络方式,勿轻信任何喊单操作。
• 欢迎投诉任何发布个人信息的行为。



